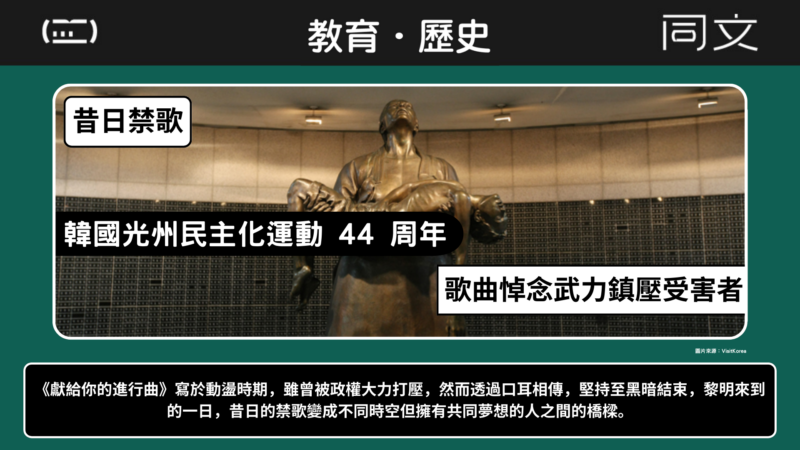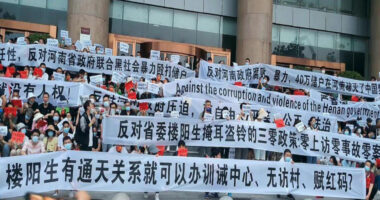轉載文章
【文:楊翠】
日常與運動,或者說日常生活與抵抗運動,幾乎是極度違和的兩種狀態。
日常,是平凡生活,日復一日,像火車軌道,在幾個固定時間,幾處定點空間,遭遇熟悉的人,做相同的事。靠著重複的時間線與熟悉的空間感,我們得以安頓自己,雖然有時無趣,但讓人安心。偶爾,小小出軌一下,到一兩處陌生地方,感受一點點時間繞行、空間探秘與新鮮遭遇的趣味。
但抵抗運動不是在日常裡的出軌、繞行,或是新鮮遭遇,抵抗運動是非日常,而且是少數人的非日常,是偶爾才出現的社會景觀。大多數人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即使遭遇了這個景觀,也會選擇默然以對,繞路而行,甚至咒罵他人的非日常干擾了他的生活日常。
然而,梁莉姿的《日常運動》中,日常與運動緊緊扭絞在一起,無法區隔分離,成為這個世代香港青年的生活現實與生存狀態。
這是在巨大的暴力與剝奪之後的殘存現實,既熾熱又荒蕪。
陳黎有一首短詩〈二月〉,描寫二二八事件後的家園裂變與日常變調,很打動我。詩中以清晨、黃昏、春天、秋天、日曆、鞋子、黑髮、腳步聲、洗臉水等日常性元素,描繪家園的尋常生活景觀,而以一再重複的「失蹤」,顯影家園日常如何一點一滴被抹除,成為深痛刻骨的失落。
沒錯,日常是無趣的,然而,如果連如此無趣的日常都被剝奪了,那麼,整個生活也幾乎不復存在了。
我經常在想,家園與日常,對人們而言究竟是什麼。家園,我們視為一處光色溫潤的所在,是生命安頓的場所,然而,也正是這個家園,總是成為強權奪取的客體。當家園被權力者侵入並附體,家園不再是安居所,家園的日常就會扭曲劣化,變成一場場惡夢,生活其間的人們,只能被惡夢吞噬入腹,殘喘、掙扎。
或者,被迫把自己也融入惡夢一景,日久成為自然,失卻原初家園的記憶,失去主體自身。
2019年6月到11月,香港城市經歷了一場巨大的剝奪。國家一聲令下,一整座城市與島嶼,所有的日常,一夕覆滅,國家暴行成為城市的新日常。這就是韓麗珠《黑日》中的「黑日」意象,也是梁莉姿《日常運動》中的時空場景。
當想像中的兩極在現實中碰撞,共時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們才覺悟到,所謂的日常,從來都不是處在天使的國度,我們的日常,原來一直都在老大哥的凝視看管之下,是它決定是否讓你呼吸,也是它可以瞬間剝奪所有空氣。
從基進的意義來看,梁莉姿《日常運動》中,日常與運動纏結絞扭的狀態,正是一種挺身奮起,與剝奪對抗的進行式。不是日常時空被運動時空覆蓋,而是家園早已裂變,日常早就失落,為了奪回家園,重寫日常,青年挺身,投入抵抗運動中。
梁莉姿所要扣問的,不是國家暴力本身,因為這是不問自明的,她要寫的,是在國家暴力四面八方環伺之下,投身運動的這群人、這些家庭、這個世代的精神紋理。
梁莉姿出生於1995年,是九○後香港作家中既犀利又溫柔的一隻筆。梁莉姿與她的世代,幾乎是同時有著熾熱青春與蒼老靈魂的世代。很年少,就彷彿歷盡滄桑。她是接受黨國教化摧眠的世代,然而,尚未體驗風和日麗的家園景致,國家暴力就撲身襲來;她曾經置身運動現場,一起在激奮與熾熱中吶喊,但也深刻見證了運動中的失落與迷惘。
梁莉姿就這樣馱負著整個世代的集體創傷、社會恐懼、身份迷思,從一大片黑霧森林中穿行跋涉而來,她想描繪的,是2019年香港城市的感覺結構,也是這個世代集體的靈魂底蘊。
她的犀利與溫柔,就是來自於這種熾熱與滄桑的高度反差,也來自於她的處身其間,更來自於她的抽身其外。她從整座落滿霉粉與硝煙的城市中跋涉而來,要找到一個抽離的書寫位置,我相信,於她,這是最艱難的一件事。
但如果沒有找到這個既近又遠、既內又外、既中心又邊緣的位置,她就無法帶我們看見香港這座城市一整個世代的靈魂樣態,她無法帶我們看見國家暴力如何侵蝕,霉粉如何紛落,以及一個世代的希望、失望,甚至絕望,還有在絕望廢墟中,那幽微而堅定的一線光。
如果她無法帶我們看見真正黑暗的底色,我們就無法指認光的意義。
《日常運動》分成「運動日常」、「日常」、「日常運動」三輯,合計10部短篇小說。結構上,各篇可以獨立閱讀,也可以串成一部長篇來讀。熊貓洪奕這個角色全書貫串,可以視為主角,但書中人物都是相互關聯的,前一個故事的配角,在下一個故事成為主角,而人物關係則是一點一點洩露拼織,以有點懸念的方式,從虛線變成實像,圖像逐漸清晰。
《日常運動》的結構,類似於組曲,但更像故事長卷,一個構圖是一個故事,整幅長卷也是一個故事,故事與故事之間有咬合感,既獨立又交織,你可以從頭看到尾,也可以從其中任選一部,單獨來看。《日常運動》的這種敘事結構,非常巧妙地呼應了「一座城市一群人的日常與運動」這個主題。
或者可以說,這種既獨立又交織的結構,就是小說中人們生命情境的隱喻,也是一座城市、一個時代的隱喻。在這個黑暗時代,在這座被國家暴力接管的城市,每一個人都彼此纏結,但又深切感到孤獨荒寒。
《日常運動》是寫香港青年的運動進行式,但不是描寫運動的慷慨激昂,不是描準運動者在運動現場的英勇與氣魄,而是將鏡頭拉遠,從一座城市,從運動的側面寫運動,從日常的側面寫日常,這是本書最獨特的地方。
它揭露了日常與運動的灰階地帶,這可能會讓許多人失望,因為它指認了我們都隱然知道,但大多數時候刻意忽略的那些運動中最幽微、曖昧、矛盾、衝突的存在。但是,如果運動與日常已然如此糾葛纏結,浪漫化的文學書寫並不會提供真正的救贖,唯有直面灰階,直面矛盾,直面內心的質疑、猶疑、茫惑,才可能在最黑暗的底色中,找到一線光隙。
大多數時候,面對黑暗比面對灰階容易得多,面對國家暴力比面對自身的內心幽微與同志矛盾容易得多。然而我們必須承認,灰階、幽微、矛盾,含藏了更多真實,不曾面對這些真實,我們永遠無法抵達美麗新世界。
因此,在我看來,《日常運動》中最犀利的地方,是日常與運動的相互詰問。梁莉姿一面以運動詰問日常的扭曲變調荒謬,一面又以日常詰問運動,這場運動將會帶領我們抵達什麼地方?能是一處清風麗景的新日常嗎?還是終將陷入無止境的纏結。
日常與運動的相互詰問,清楚揭露了一個困局。當日常是日常,運動是運動時,主體可以透過生命時間與生活場域的交替,尋求呼吸換氣;當你投身運動時,彷彿為蒼白無力的日常點燃希望,當你回返日常生活時,又可以充電蓄能,等待下一場戰役。然而,當國家暴力逼使人民的日常與運動緊緊絞織在一起,日常不再是運動的後台,也無法成為換氣的窗口,《日常運動》中,那些孤獨、荒蕪、鬱苦的靈魂,連自己都分不清,這些痛苦究竟是緣於日常的蒼白或是運動的磨蝕。
日常與運動的相互詰問,它的意義不在於最終答案,而在於主體的自我思辨。主體在理想、行動、奮起、困挫、失落、幻滅,還有在親人、愛人、運動夥伴之間的彼此傷害與相互舔撫中,直面自身。
那是他,也是你與我。小說中,每個人的生命都在掙扎,都有破洞。或者無法忍受母親對待運動的虛矯,或者長期擱淺在母親的生活掌控中,或者對於自己能在街頭衝鋒陷陣,卻無法在日常工作場域中對抗體制而感到分裂痛苦,或者對於殉身者與被捕者傷痛自責,對於撤離者的離去失望憤怒,或者經歷從中國到香港的身份認同迷惘。
更有為在亂世裡荒蕪而熾熱的愛情而心痛。紛亂時代,沒有人能以你想要的方式來愛你。小說裡有這麼一段話,很精彩:「這世界瘋了。所有人的痛苦和憤怒,它們無法被校準成統一絕對的瞄頭向仇恨對象發射,遂成黴菌,粉粉落落,繁殖,飄飛,無定向,濡濕霉爛,滲鑽所有人的鼻腔。」
誰都不能真正撫慰誰,暗夜裡每個人都只有自己。但是,在寫出這座城市的黑霉底色之後,梁莉姿卻拋出這麼一句話,做為全書結語:「樹縫有光,天要亮了。」
明日天光,在這座霉粉持續紛落的城市,一個個行動主體仍然會從威權廢墟中爬起,繼續奪回被竊取的家園,重寫被偷換的日常。
因為,光,不是意義本身,追光的行動,才是意義所在。失蹤的日曆終將不復重返,但每一張行動者的新日曆,每一次薛西佛斯的行旅,都會在城市銘刻下來。

-800x450.png)
-800x450.png)
-800x45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