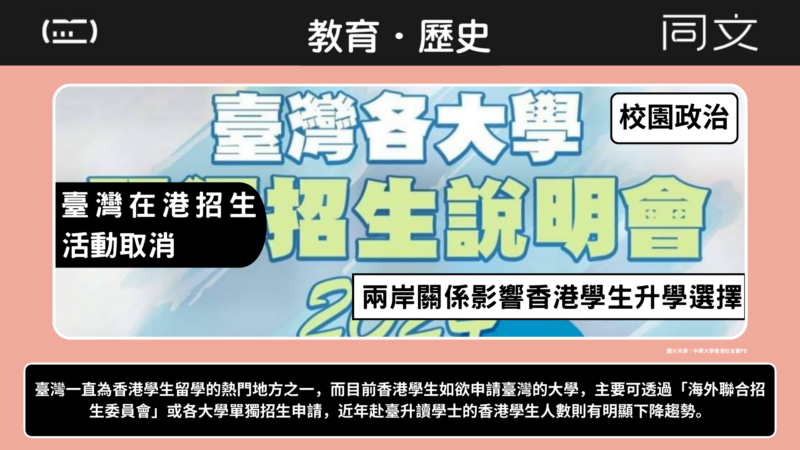【意志】
他們在場上拼命跑動,死纏爛打,瘋狂逼搶。看著這一切,差點讓人忘卻,眼前的球隊是我們的香港隊,是在極殘缺的備戰條件下挑戰亞洲列強的香港隊。
那趟如夢魘般的印度之行,已是一個多月前的事。旅程結束,球員紛紛返港,被困在酒店一周,狀態已跌大半。隔離過後,又正值休季,球會大多仍未開操,港隊在長途跋涉後和部分球員征戰亞協下,亦沒理由繼續訓練。於是,直至東亞盃揭幕前一周展開集訓時,大部分球員已有近一個月沒正式比賽和操練(有份踢亞協的便兩至三周)。
運動科學角度來說,停止操練兩星期,便可稱為Detraining的狀況,球員的攝氧量、衝刺和跳躍等能力都會明顯下降。歐洲球會在休季幾周後,一般至少會在開季前四至五周復操,復操七至十日後踢首場友賽,但亦只會讓球員上陣45分鐘。
安達臣和梁冠聰在訪問中都有提過備戰不足的問題,但只有這樣看,才能理解在停操幾周和集訓短短一周後,用那仍然遲緩沉重的身軀,一邊與對手抗衡,一邊與身體的界限周旋,出戰聯賽正踢得如火如荼、狀態處於頂峰的日本南韓隊,是多麼瘋狂的事。也只有這樣,才能理解在這處境下能令南韓吃些苦頭,又令中國球員狼狽得像便秘一樣(中國媒體的描述),是多麼的不可思議。
那幾星期間,雖然沒正式訓練,也是舟車勞頓後和漫長球季前的僅有休息,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的球員從未怠惰下來。可能是在隔離酒店床邊兩米闊的窄巷,或家裡廁所門前的瑜伽蓆上,或是在那人潮如湧的運動場跑道,或佈滿在野餐放狗的途人的海濱公園,但他們一定沒有怠惰下來。一直在堅持操練,一直在默默付出。
我曾嘗試代入他們,幻想久未比賽、狀態欠奉的自己,站在立鹿嶋足球場的草坪上,望著對面熱身的全是日職猛將,又想起家鄉數以萬計球迷的關注與期盼,感覺到底會是如何?對體力不繼和抽筋的焦慮?對出醜的擔憂?還是對大敗的恐懼?在他們身上,似乎通通都沒有,至少在三場比賽都看不到。而看到的,就只有默默付出的成果,和一份足以超越身體限制、令人動容的強大意志。
【戰術】
但終究我們還是三戰全敗。由亞洲盃至今,我們在安達臣帶領下改頭換面,感覺煥然一新,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可能性,但在戰術和個人層面,漏洞和改善空間始終存在,而且有些是顯而易見的。
死球防守
最大問題必定是死球防守。對阿富汗的失球,對印度的頭兩球,日本的短角球攻勢,及中國兩次黃金機會,都是來自死球。而當中更沒有一球是被對手壓著來頂的,與身高和體格毫無關係,問題全然在於部署和空間控制,即安達臣的戰術安排。
在防守角球時,現今很多教練會要求十一名球員都退回禁區,或是禁區外圍的2nd ball區域。比較進取的,也只會留一名球員在中圈附近以備反擊。但安達臣聽聞在北韓年代起,已偏好擺三名球員在中場線,三人左中右一字排開,目的既是牽制對手的進攻人數,也是為反擊而作的賭博。此外,以兩名球員分別駐守前後柱,這在頂級足球已近乎絕跡、被定性為亡羊補牢的部署,安達臣對它卻情有獨鍾。
以上兩項部署,令我們在禁區內不時處於人數劣勢,不夠球員盯人,不夠球員執第二點,而且從來沒有堵塞重要區域的Spare Man(敢說我看過的所有人盯人防守,都至少有一名守zone的球員),外圍的2nd ball區域空空如也,短角球防守亦往往要以一敵二。
六場比賽以來,反擊未曾成功,防守倒是漏洞頻頻。那些失球中的走甩對手、混亂中被補中、禁區頂被射入、短角球二對一,全是人數不足和沒有堵塞重要空間的後果。這是我們最致命的問題,但也是最易修正的問題。
陣地防守
壓逼和陣地防守的部署也值得斟酌,但問題比戰果反映的細。據球壇知名的分析平台Wyscout的數據顯示,我們對印度、日本和南韓,三場大敗的比賽中,Expected Goals分別是(0.96 – 2.2/0.08 – 2.55/0.54 – 1.2),即對手的平均入球期望值為2球左右,但我們卻平均每場失了4.5球。兩者的差距,多是門將和運氣使然,相信葉鴻輝的回歸,部分問題便會迎刃而解。
對於防守時的戰術運用,最大質疑在於對4-3-3陣形的執迷。網上的主流論述,一直圍繞安達臣應否堅持高位壓逼。對此,我在之前的文章已詳細解釋過壓逼帶來的優勢和重要性,而且事到如今,也知道安達臣不會毅然捨棄個人風格。因此,我認為問題不應在於是否壓逼,而在於怎樣逼,用什麼體系逼,和是否每場用一樣的體系逼。
要知道,現時安達臣運用的4-3-3陣形和當中的戰術要求,環顧歐洲五大聯賽,除了壓逼和跑動能力首屈一指的利物浦之外,就很少球隊會恆常使用。大多在控球時踢4-3-3或4-2-3-1的球隊,如曼城、巴塞和阿仙奴,甚至傑志和理文,在壓逼和防守時,都會以不同形式將陣形調整為4-4-2或4-1-4-1,而不會將兩邊翼鋒如此進取地放在第一道防線上。
我們的體系和戰術細節,幾乎是利物浦的複製品:4-3-3的起始陣形,兩翼內切向中堅或門將施壓,中鋒則看守對方防中;若皮球去到邊路,兩邊中場黃威或陳俊樂移到邊路施壓,填補兩翼上前而留下的空檔。簡單而言就是這樣,好處主要有兩個:一,壓逼由兩翼帶動,翼鋒由邊路,即中堅的盲眼位,向他們施壓,中堅的選擇剩下回傳予門將或Ball side的中堅, 是對控球方最不利的選擇。此外,不尋常的壓逼角度,亦會令一些中堅無所適從;二,兩翼壓前,球隊一旦重奪皮球,他們便自然處於靠近龍門的位置,對反擊固然有利。
但弊處,或很多世界級教練也敬而遠之的原因,則在於第一,它要求翼鋒向中路壓逼,中場填補邊路,閘位要適時上前。這些細節,對球員在移動、補位和對體系理解的要求較高,較難執行。第二,也基於同樣原因,它對個別球員的體能和防守意識很高。第三,因上述翼鋒和兩邊中場的角色,往往會削弱對兩閘的保護,兩閘會更常被孤立,陷入一對一、甚至一對二局面。
而上述這些缺點,亦有在我們的比賽中暴露出來。若來年要在亞洲盃走得更遠,最理想是能再建立出多一套體系,可以是最簡單直接的4-4-2,或是善用羅梓駿的特性,在壓逼時形成五人防線,讓我們具備應對不同戰術特性的能力。
【身份】
2015年的中港大戰過後,有學者的研究指出,這場比賽和連帶的海報事件,源於兩地對民族主義的不同理解,說明體育是一個讓人界定、協商和重構民族身份與邊界的場合。當時反映,中國的民族主義強調族裔和血統,而香港在種種歷史和政治因素薰陶下,滋養出一種一方面講求公民身份,而另一方面亦以共同文化、符號和記憶為基礎的身份認同。
每次對壘,都是一次國籍、背景、志向和信念迥異的人,背負著各自的民族身份,在此場合中並置與碰撞。同一空間,兩件球衣,兩個民族,但有二十二個故事:有人是生於巴基斯坦,十歲來港,為代表香港而犧牲了自己和家人本來的國籍;有人是生於香港,十歲離港,為代表中國而犧牲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有人是生於香港,志於香港,但在中國聯賽效力;有人是混血兒,成長於香港,也樂於代表香港,但外貌和血統與眾不同,其志向和價值觀近來亦備受批評。
近年,對香港人的定義,對此民族的劃分,早已超越族裔,超越公民身份,文化和語言亦漸顯不足。但更根深蒂固的是什麼?是一種心之所向的自我認知,一種對這民族本身的價值取態,還是一種共同的信念和生活實踐?對一個民族而言,似乎沒有比釐清邊界和梳理差異重要的問題,而足球這個場合,則為此提供了一個具體而實在的獨特素材和視角。
參考資料:
Lawrence Ka-Ki Ho & Andy Chiu (2017): ‘Indigenous’ or ‘All Stars’: Discourses on ‘Team Hong Kong’ in a FIFA World Cup Tournamen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DOI: 10.1080/09523367.2016.1267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