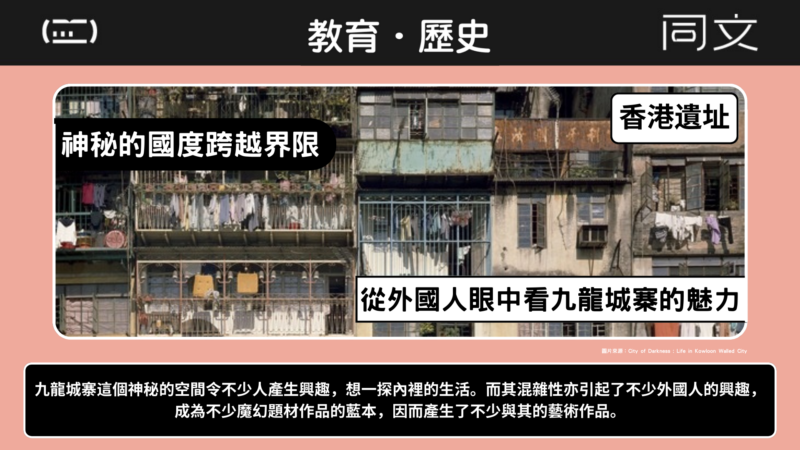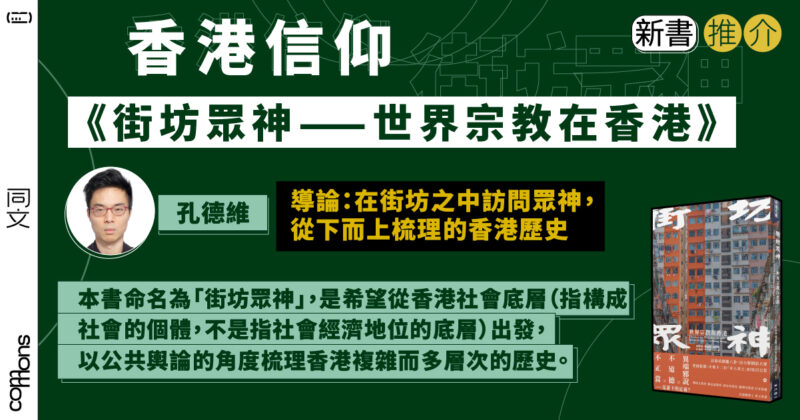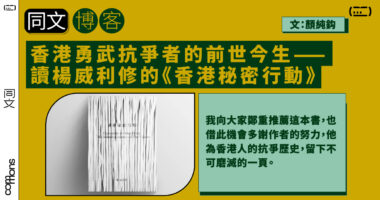文:孔德維(沙烏地阿拉伯費薩爾國王與學術及伊斯蘭研究中心研究員)
雖然現在在香港或臺灣的咖啡廳與陌生人搭訕會一般都會被視為「痴漢」(這當然視乎搭訕者的顏值),但在十七世紀末咖啡和茶葉融入西歐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後,咖啡廳、茶室、沙龍,甚至是劇院、博物館和音樂廳就成為了社會學家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理論的物質基礎。所謂的「公共領域」,是指介乎於國家與社會(即國家所不能觸及的私人或民間活動範圍)之間,公民自主地了解、參與公共事務的地方。在前工業資本主義興起的時代,城市居民在西歐工業國家獲得了新的自由,從此進行政治統治的「國家」(state)與私人生活(privacy)之間就形成了一個介乎兩者之間的公共生活領域,由受教育的中間階層所主導,當中形成的意見就代表了「社會」(society)並與「國家」互動及抗衡。哈氏假定了「公共生活」的主角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知識人,他們在咖啡館、茶室、沙龍裡討論著學術、藝術、社會和政治等議題。 但咖啡店常客的討論話題是否如哈氏想像的充滿「公共性」(publicity)當然惹人懷疑,畢竟鄰家的太太的偷情對象是不是通渠工人,較於城市的溝渠設計更能惹起討論者的興趣。
「公共領域」與街坊
然而,公共空間的關鍵其實可能在於陌生人得以在該場域中互相交流資訊,而資訊交換的內容反而是次要的事項。哈氏的理論以國家、社會作為框架開展有關於公共性的討論,所提出的公共領域理論亦是以政治參與(political engagement)為基礎。 然而,單純地以「人類社群互動」為中心思考公共空間的意義,其實不必然要以政治作為唯一關懷。羅賓.登巴(Robin Dunbar)從人類學與演化心理學的角度提出了「八卦」(gossip)作為人類社會營運的基礎。登巴認為早在文字史料出現以前,原初社會的部族成員需要在艱險的環境生存,有賴於與其他成員建立關係,並判斷不同成員的可靠程度。他提出「八卦」在人類群體中起了像其他靈長類動物間互相梳理毛髮的互惠(reciprocal)作用:當某一成員允許另一成員為其提供服務,他們就在一定程度上建成了互惠聯盟。
然而,當人類社群發展得越來越大,梳理毛髮等靈長類動物應用的個體對個體結盟方式已變得過於耗時。至此,人類逐不得不發展出更高效率的結盟方式。通過語言(也就是「八卦」)對某人作出評價,從而分辨出社群成員中誰是叛徒、誰是可靠的人,其實就是以互相傳播信息的方式來建立聯盟。以信息交換建立與維繫社群,既能使具「非親緣性」(impersonalize)的訊息傳遞者之間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亦能以輿論影響群體內外的人。 由此看來,咖啡館、茶室和沙龍中的對話,就很自然地是對鄰家太太與通渠工人的關係抱有滿滿的興趣,而對城市的溝渠設計鮮有論者問津。歷史上,「政經」與「八卦」本質上不互相排斥,但當成員間長期互動後,「有用」資訊很可能就由社群成員的道德倫理轉而為整體社群的生活條件與秩序提升。在這種處境下,城市的基礎建設與秩序建立,也有可能比鄰居的性觀念更能吸引討論者的興趣。
哈伯瑪斯以政治為出發點的公共領域理論關心的是公共生活的秩序,羅賓.登巴從演化角度提出了「八卦」理論則將對話的起點置於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這兩種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觀點都指向了資訊交換活動對於建立與維繫群體的功能。公共生活顯然就是資訊交流延伸,而在交流的過程中得以形成的往往不止是各種輿論與觀點,而是參與者之間形成了群體。如果如同哈伯瑪斯一樣以交流的空間作為出發點,讀者很容易就會發現交流的空間、參與交流的群體與群體所共同信納的輿論以或鬆散或緊密的形式連結在一起。 如果說十七世紀末的西歐以咖啡館與茶室構成了近代公民社會的空間、群體與輿論,國際貿易頻繁的華南海岸與東南亞的社會同樣形成了具自身特色的版本。
事實上,早在十三世紀的華語使用者就將以描繪「空間」的詞彙借代「空間」所衍生的群體。中國元朝的孫仲章在《勘頭巾》就提到「若不看解勸街坊面分,小後生從來火性緊,發狂言信口胡噴」,當中「街坊」一詞由原先代表街道(街)與當中可用空間(坊),延伸至指涉社區使用者所組成的群體。 「街坊」的意義對今天非粵語族群來說較為複雜,一般華語語系使用者鮮少在日常應用此詞,惟在粵語仍為常用詞彙,多指「住喺屋企附近、當區街道嘅人」(住在家附近、該區街道上的人)。 「街坊」的這一應用方式,與十八世紀末廣州「城鄉合治」的基層街區單位較為類同。學者賀躍夫留意到廣州的基層街區單位有「街」、「坊」、「巷」、「里」、「甫」、「約」等不同名目。帝國政府城市居民的管理類同於鄉村的自治組織,以地鄰為原則編成「保甲」,在不同地方單位設立地保以維繫介於社區與政府之間的溝通。在英國外交官密迪樂(Thomas Taylor Meadows)筆下,廣州城的地保在空缺時,地方單位會貼出需求地保的告示,一眾最具勢力的戶主再在寺廟中選出新的地保,由街坊籌組經費支薪,再稟請縣衙門任命,在絕大部份情況「街坊」的決定均會獲得帝國在地代表的認可。 這種自治類同於華南鄉村社會的「鄉約」,其於十八世紀末的廣州城又會以「街」組成的「坊」為單位,可以被稱為「街約」、「甫」(鋪),或是其他稱謂的單位,但大抵都具有自治與自衛的功能。
賀躍夫引用了粵海關的報告指出十九世紀末期廣州街坊大多以街坊為單位籌集經費自我防衛,一眾大戶更往往必須維持一支民兵以保衛自身的街區。他們顯然對帝國提供的保障失卻信心,故當地方政府試圖集中街坊自籌的經費中央調度時,街坊乃極力抵制。 這種地方自治的力量在大清帝國力量減弱時曇花一現,但卻在日後中國政府現代化的進程中漸次消散,「街坊」也因此從具政治權力的實體轉而為社區的概念。 而在同時代的英屬香港,強而有力的現代化政府並未有容讓「街坊」掌握到民兵的合法武裝力量,「街坊」的含義更為類同於生活在同一空間,而具有營聚力的非親緣性群體,也就是指聚在一起交換情報和資訊(八卦)的共同體。
本書命名為「街坊眾神」,是希望從香港社會底層(指構成社會的個體,不是指社會經濟地位的底層)出發,以公共輿論的角度梳理香港複雜而多層次的歷史。七○年代在香港大學擔任研究員的濱下武志曾在《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提出香港曾經一時面向四面八方、擁有八大腹地的海洋性格,當中幾乎囊括了人類歷史上絕大部份的宗教。 印度教、瑣羅亞斯德教、猶太教、中國宗教、佛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錫克教、巴哈伊教,以至種種新興宗教與靈性運動,都可以在香港同時並存及發展。如果由宗教的角度出發,幾乎所有宗教的教義都具有一定的排他性(exclusiveness)。在全球化退潮的年代,不同的主流社會都對各類型「小眾」重新施加壓力,美國的聖經地帶(Bible belt)、緬甸的羅興亞區域、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國有舉世矚目的案例,而在其他國家亦逐漸浮現。無論一神或多神的信仰群體,類近的宗教衝突也多有發生。
由此角度觀察,香港存在著種種來源不同的宗教信仰,卻未有出現教派之間的勢不兩立,其實是十九世紀以來的重大奇蹟。香港的陳慎慶教授在二○○二年出版《諸神嘉年華:香港宗教研究》最早系統地回應了這一現象。受基督宗教神學與社會學訓練的陳氏在書中說明了香港各個宗教信徒人口的比例、社會特徵和價值觀,再以中國宗教、基督宗教、回教及新興宗教四個案例說明了香港宗教大體和諧共處的「精神面貌」。 陳慎慶的介紹在二十一世紀初期獲得香港宗教界不同回應,在論述範式層面頗具突破性的一個例子是二○一七年李樹甘、羅玉芬、林皓賢、黃樂怡等編著的《香港宗教與社區發展》,李氏等加入在原有論述的基礎上更細緻地將道教、佛教分別處理,在保留「基督教」(意指整體的基督宗教,Christianity)與伊斯蘭教的同時,將討論擴充到其他小型宗教。《香港宗教與社區發展》尤其重視宗教與社區網絡間的互動,以宗教組織與信仰的角度陳述了不同宗教藉教育、醫療、安老等不同社會參與(social engagement)建立了現代香港的融洽公民社會。
《街坊眾神——世界宗教在香港》早鳥優惠購買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