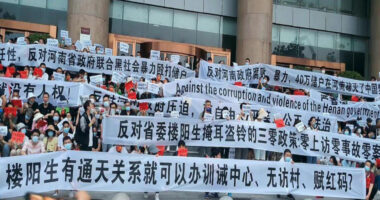同文博客
英國流散香港人群體於 2019 年開始的移民潮開始慢慢形成,經歷一年多的發展,流散香港人群體由起初衣食住行不同環節的適應,趨向想像如何在新生活自處,而文化身份議題往往在生活政治的反思中體現。而筆者前線與街坊接觸的經驗觀察到流散香港人正處於身份重塑與生活政治的重新交織的過渡期,過程中往往都會經歷到因失去自我實現(self-actualisation)的連續性而感到的哀傷(grief)。本文希望由筆者的前線觀察,以生活政治的角度探索流散香港人身份的內涵。
流散香港人身份與生活政治
流散香港人身份是一個複雜的文化政治議題,在現代社會的個人化和多樣化的生活政治脈絡中更看似無跡可循。流散香港人身份是一個流動(fluid)的概念,即是就著不同的社會情景,加上當時人個別背景和人生經驗,最後呈現不同的演繹方式和型態。例如在英國流散香港人社群時常出現的港英中身份拉扯中,流散香港人身份可能就著自己對香港人、英國人和中國人三個文化身份有一套自己的演繹,有著不同層次的見解。可能,在「圍爐」時,香港人的身份會明顯突出,發展的同質偏好(homophily)作為建立社區互助網絡的基礎。在日常融入社區集體生活,成為一名普通街坊時,香港人和英國人的身份可能出現交錯顯現、甚至出現混合轉化的情況。早前英國的區議會選舉,流散香港人社群一邊作為香港人,在慣常的社交平台網絡中以香港人的身份互相幫助,另一邊都會討論作為一位英國選民,怎樣認真參與選舉和投票,由確定選民身份、找票站、填寫選票到了解候選人背景和政綱。
然而,香港人和英國人的身份出現混合轉化的情況有機會在以香港人為主體向社區人士互動時出現。筆者日前跟幾個香港人街坊義務向社區中一個童軍組織介紹香港文化,很有趣是我們跟本地的童軍搞手討論活動內容和流程中,會以一個居於英國的香港人角度編排怎樣介紹對香港文化的「集體想像」(筆者按﹕因為事實香港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樣,所以美好都只是存在於大家的回憶和想像)。在過程中,就著聽眾的文化背景,大家其實很仔細去整合香港「集體想像」中的生活、文化和歷史特徵,怎樣可以由聽眾的角度一步步引領她們了解香港文化。無論在籌備和當晚活動的過程中,跟搞手的彼此的互動,尤其是看到一眾八到十歲童軍感到歡樂和接納,覺得了解香港是社區裡一件有趣和享受的事,都令筆者覺得流散香港人的文化身份社區集體生活中「係有 D 用同價值」,筆者和街坊都是轉化為一個「普通街坊」的身份在社區互動。
由於流散香港人身份具有流動的特性,而在現化社會中的脈絡中,筆者觀察到街坊的文化身份這個政治議題多於反思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不同的生活政治中呈現。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是英國社會學家 Anthony Giddens 於 90 年代初提出,他指出傳統文化的鈕帶因為現代化和全球化下加速鬆綁,每個人都(相對傳統社會時期)得到更多的選擇,而對政治議的參與都傾向由個人生活的選擇和反思出發,所以政治參與往往是一個對實現自我(self-actualisation)的伸延。因此,筆者記得在元宵的放映會活動座談會環節,討論到流散香港人身份的議題怎樣探索,街坊和講者分享的觀點都包含著不同的選擇和取態,例如流散香港人身份的議題是怎樣與社區產生聯繫才能開展、怎樣在日常生活中「滲」著香港人身份的特徵與其他社區人士互動、來到英國就要做一個英國人和流散香港人身份就是持著信念,活好每一天等。但是,流散香港人身份能夠仔細反思生活政治其實都不容易,因為這波的流散香港人都經歷過或多或少的失去與哀傷,似是一個隱蔽的傷口,時不時隱隱作痛。
流散香港人經歷的失去與哀傷
這波英國流散香港人不似以往香港的經濟移民,心態上不是 King Sir 所講「覺得頭上有片瓦, 腳下有塊土地係唔夠既,所以佢地不惜離鄉別井,漂泊半生,走到偏遠既世界角落去打工……」做一個紮根香港、背靠中國、面向世界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 這波是因為對政治環境的憂慮而放棄香港所有的東西,甚至全家幾代同堂在英國重建家園。這個家庭決定,除了放棄了在香港的事業和經濟收入,同時放棄了在香港習慣了的生活方式,更重要是中斷了自我實現(self-actualisation)的連續性和支持著自我認同的社交和家庭關係。簡單講這是一個個人發展的危機,結果更可以是一個動搖自我存在的不安感(ontological insecurity)。
每個英國流散香港人都經歷不同程度的過渡走出這類「失去」(loss)的經驗和哀傷(grief),過程中透過生活和文化身份重新交織最後「重新上路」,例如為自己重新訂立人生目標、討論在英國的人生規劃、重新認識新朋友、在英國找工作、重新建立生活習慣、重新認識英國的社會文化、最重要是重新認知自身信念和價值(何謂對錯好壞順逆福禍)。借用出生瑞士的美國精神病醫生 Elisabeth Kübler-Ross 於 On death and dying 一書中提出人面對失去摰親或面對災難出現的哀傷有五個階段(five stages of grief),分別是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抑鬱(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這類精神和心理反應未必是線性發展,又會來回又折返,但是大概都能夠形容英國流散香港人在這個過渡期的精神和心理狀態。而且,在打擊「放負 L」的政治考慮下,大家都習慣變得更加抑壓,對自己表達和回應感受更加苛刻。在筆者在前線的觀察,每個這波英國流散香港人都經歷不同程度的失去和哀傷,但不是每個都相信在接受新變後,成功重塑身份和交織生活達到個人成長之前是可以講 it is ok to be not ok,接納社區已經為香港人而設的協助。
最後,筆者討論前線觀察,不是企圖最後發放正能量,呼籲大家「香港人,加油!」 ,而希望指出流散香港人這個議題是可以由生活政治去理解,而生活政治往往是扣著一個失去與哀傷的集體經驗。反而,觀察生活不同環節對身心社靈的影響,回應自己和身邊親人朋友的感受,可能是重塑流散香港人文化身份,融入英國社會的另一個路向。

-6-800x450.jpg)
-800x450.jpg)
-800x450.jpeg)
-1-800x450.jpg)